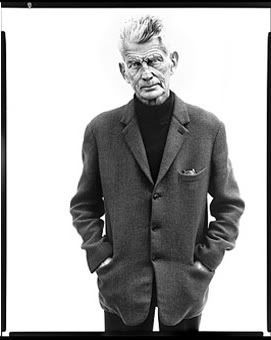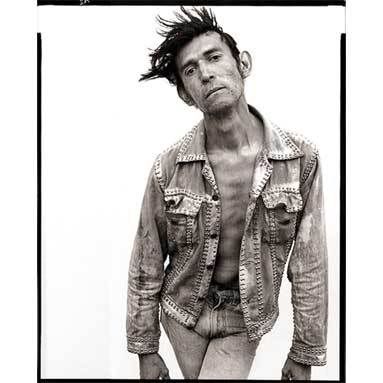对冯至没有太多的了解,只模糊记得大学现代文学史课本上,提到他是“浅草”“沉钟”的成员。后来读到里尔克的一些诗,也有冯至翻译的,可是从来不知道他还写小说。
前不久“闲闲书话”上有人推荐《伍子胥》,“中国的奥德赛”云云,一时好奇,便找来读了(基本是在马桶上读完的)。 这是个中篇,很好读,文字极细腻,还很少有小说的语言能给人“炼字”的感觉。随手拈两句:
“第二天的阳光有如一条长绠把他从深处汲起。”小说从伍子胥在城父等候父亲的消息写起,描述伍子胥一路逃亡到吴国投奔夫差的过程。有意思的是,小说并没有写伍子胥如何见吴公子光以及如何灭楚复仇,而是到伍进入吴国集市就嘎然而止。冯至显然对伍子胥的种种英雄壮举没有兴趣。伍子胥逃出城父时孤身退敌,估计比《墨攻》里刘德华在城墙上那一箭还要帅,可冯老先生居然就淡淡地说了一句:
抄一段小说的开头:
“城父,这座在方城外新建筑的边城,三年来无人过问,自己也仿佛失却了重心,无时不在空中飘浮着,不论走出哪一方向的城门,放眼望去,只是黄色的平原,无边 无际,从远方传不来一点消息。天天早晨醒来,横在人人心头的,总是那两件事:太子建的出奔和伍奢的被囚。但这只从面貌上举动上彼此感到,却没有一个人有勇 气提出来谈讲。居民中,有的是从陈国蔡国归化来的,有的是从江边迁徙来的,最初无非是梦想着新城的繁荣,而今,这个梦却逐渐疏淡了,都露出几分悔意。他们 有如一团渐渐干松了的泥土,只等着一阵狂风,把他们吹散。”